庙上的学校
 222
222
点击播报本文,约

 |
我跟随母亲再访我的出生地,安徽六安一个名叫骑龙庙的小村,弟妹们陪同。我们驾驶一辆商务车,在骑龙庙所属的江家店镇稍作停留,又接上母亲当年的两个学生,一行人驶往3公里开外的骑龙庙。
根据导航,车停骑龙庙,可眼前却是一座新建的砖厂。一脸疑惑的母亲刚走下车,砖厂的工人间就有人高喊:“蒯老师!”这人原来是我的童年玩伴,他竟然还能一一说出我和弟妹的小名。经他指点,母亲才意识到,她和父亲当年工作过的骑龙庙小学旧址就是眼前这间码放砖头的库房。母亲来回走了几步,停在厂房中间偏北的一个位置,语气肯定地说:“这就是那棵大白果树所在的地方!”
1955年,毕业于六安师范学校的父亲来到骑龙庙小学任教,3年后的1958年,母亲从金寨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来到这里。他俩的相遇是偶然的,是命运使然,而他俩的相爱却几乎是必然的。父亲祖籍山东,将近一米八的身高在当地算是打眼的,他又生着标准的国字脸,浓眉大眼,还总是满面笑容。母亲生在上海,她父亲是上海滩一家小纱厂的老板,新中国成立后她才随父返回原籍合肥,在合肥三中毕业后考入金寨师范。在上海和合肥长大的她,身上的“城市范儿”在当时想必是有目共睹的。这对金童玉女是方圆几十里仅有的两个外来人、城里人和文化人,他俩当时如果没有相恋相爱,反倒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一年多之后的1959年底,我出生了,出生在骑龙庙小学。
我不记得骑龙庙小学当年的模样,也没见到过当年的照片。20年前,我和父母回去过一次,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个由十来间房子围成的正方形庭院,房子破败不堪,课桌椅破破烂烂,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在院子里翻晒萝卜干。不过据父母说,他们来到这所小学时,学校的所在地的确是一座庙。在这所建在破庙上的学校里,我的父母一干就是五六年。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很少言及他们当年的艰辛,但通过他们后来偶尔吐露的只言片语,我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和工作场景。母亲说过,她生我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接生的;她去洗衣服要先用棒槌砸开池塘里厚厚的冰层;我吃不上奶,是外婆从合肥送来几罐炼乳才救了我的命。父亲说过,当年学校很荒凉,唯一的邻居就是马姓猎户,他以打野鸡、野兔为生,学校四周树木林立,夜间甚至会听到狼嚎……母亲提到的那棵大白果树(即银杏树),我倒是有一点印象,记得旁边还有一棵桃树。
我的父母是城市户口,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生活在城里,他俩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生,以他俩的学历和人脉,在县城甚至省城找一所学校当老师,应该不难。但是,他们却在骑龙庙小学这所“初小”(初级小学,即只有3个年级的小学)默默地工作,直到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一所“完小”(完全小学,即有6个年级的小学),那是一所建在一个稍大的庙里的稍大的学校——南岳庙小学。
我们驱车前往南岳庙。母亲看到车窗外的电线杆小声告诉我,当年她带着我从合肥返回骑龙庙,在江店下车后要步行回骑龙庙。她把我用布带捆在后背上,两手提着从合肥带回的行李。步行途中,她会数路边的电线杆,每走5根电线杆,她就会背靠着电线杆,喘上几口气,再继续前行。
较之骑龙庙村,南岳庙镇要大上数十倍,当时可能有数百户人家,是远近闻名的集市。每天早晨,唯一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叫卖声此起彼伏,街道的中心位置还有百货店、供销社和铁匠铺等店铺,俨然一座微型城市。位于镇东头的小学更是气派,有数十间房舍,校门又高又大,记得有一道很高的门槛,当时才三四岁的大弟很难迈过,他就会先侧趴在门槛上,然后顺势翻过去。院里两侧的厢房依地势逐渐升高,使得大门正对的正殿显得很威武,这里成了学校的大礼堂。校门前有对石狮子,我和大弟时常骑在上面,俯视门前的操场和池塘,就像一对小门神。
我们是在傍晚到达南岳庙镇的。下车后走在镇里的街道上,我们试图找回儿时的记忆。街道的位置和走向依然如故,只是屋顶的瓦片换成了彩钢板,店铺前的木板门也都换成了防盗门。街道上一片沉寂,突然,迎面走来一个女子,她借助微弱的光线居然认出了我母亲,惊呼一声:“蒯老师!”然后便冲四周大喊:“蒯老师回来了!”刚才一片沉寂的街道顿时响起几下开门声,一转眼工夫,母亲身边就聚起了好几个当年的学生。这场景十分感人。无论是在骑龙庙,还是在南岳庙,人们都能立即认出多年未见面的老师,这或许也证明了,他们当年的老师、我的父母,是他们一生中记忆颇为深刻的人物。
父母当年工作的这个地区为何有如此多的地名带有“庙”字呢?据母亲的一位学生讲,这跟当地民间传说有关,我却愿意给出一种更平实的解释。被闲置的庙宇用来开办学校,是物尽其用,构成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举动,即学校代替寺庙成了老百姓寄托希望的新处所。
当时因为各种原因,父母曾主动要求到一所大队小学——殷家畈小学教书,后来大约因为工作出色,又从殷家畈小学被调至公社所在地,负责创建分路口中学。他们白手起家,在一片荒山头上建起一所初级中学。几年后,父母又被调往独山高级中学,然后再调往六安县委河西党校执教,直至退休。
在乡村学校工作期间,我的父母要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但对于那些比我们更穷的学生,清贫中的父母总是乐善好施,他们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垫付学费,我们兄妹几个常发现自己为数不多的衣服会突然出现在某个学生的身上。我的父母会一次次地家访,说服那些不让孩子继续上学的家长改变主意。他们会把他们的学生带到合肥参观,赤脚走在省城马路上的那支学生队伍曾引来路人诧异的目光。后来,较之于我们兄弟姐妹,他们的许多学生都考上了更好的大学,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许多学生至今依然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从未高谈阔论过他们当年扎根基层是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相反,他们更多地说是为生活所迫,为稻粱谋,他们把在乡村里教书30年当成一件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无意识”证明了他们的作为之重要、之崇高。正是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我父母这样的人曾在中国最贫瘠的文化土壤上播撒知识的种子,维系了乡间的文化香火。没有他们这样的人坚守在乡村的学校,就很难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改革开放后步出乡村,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
如今恐怕很少有建在庙上的学校了。庙上的学校逐渐被各种现代化的学校所取代,但我希望中国乡间的文化味不会淡化,中国社会需要文化的圣殿,也需要知识的庙堂。
《 人民日报 》( 2025年09月13日 08 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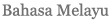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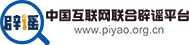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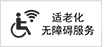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